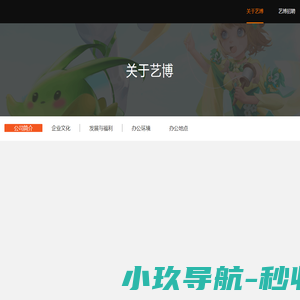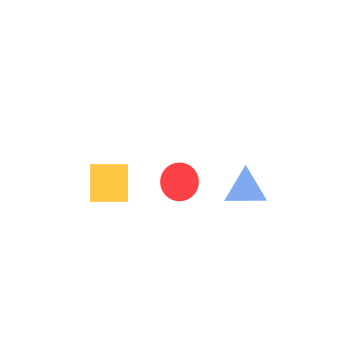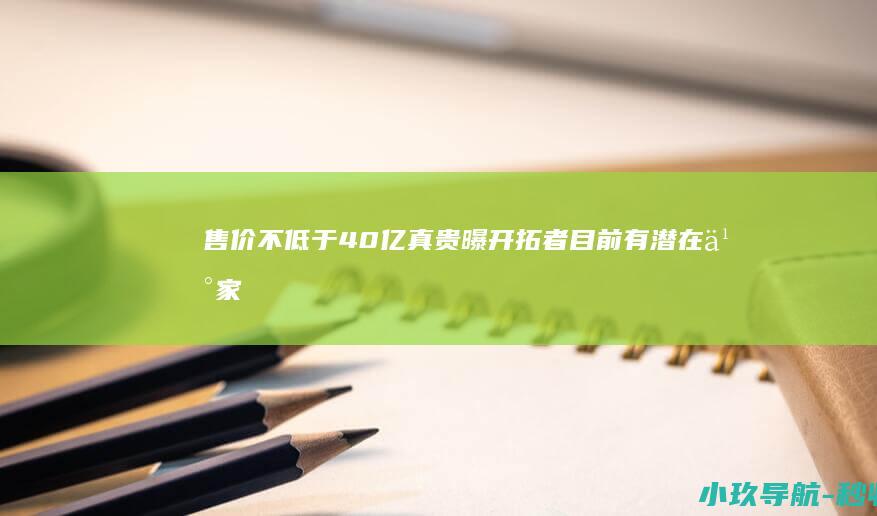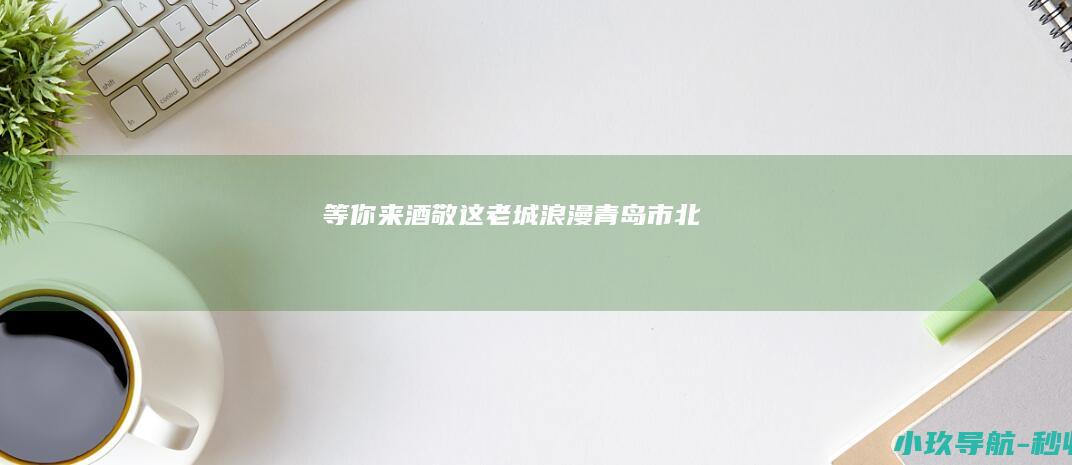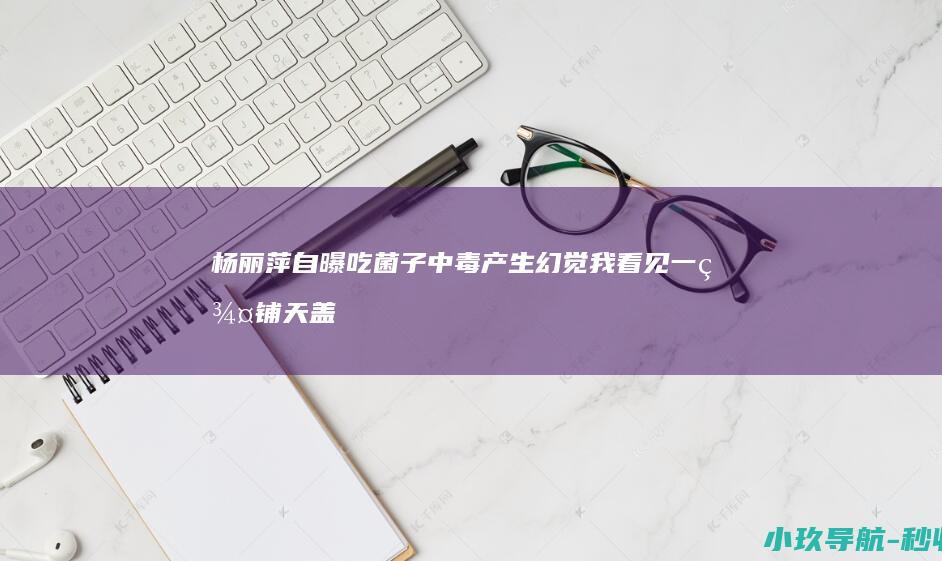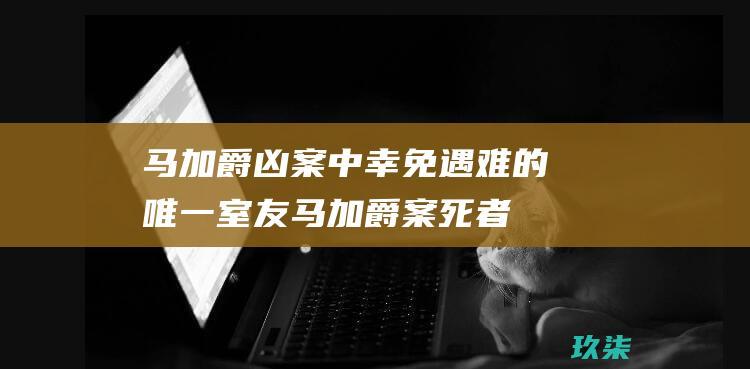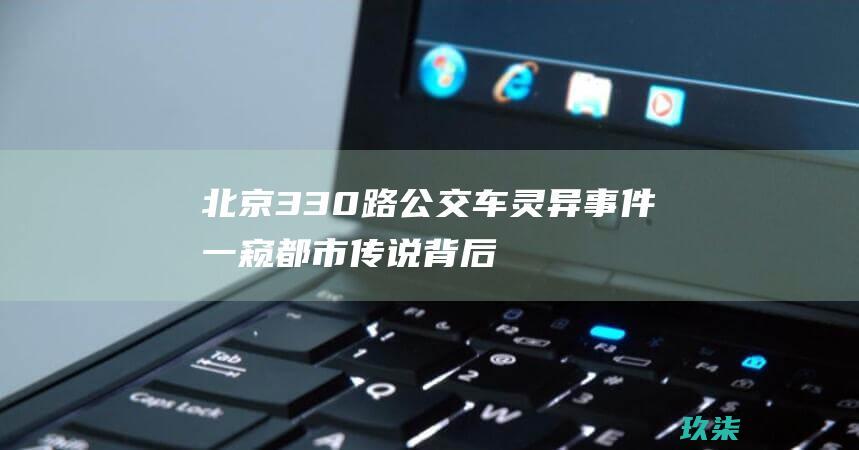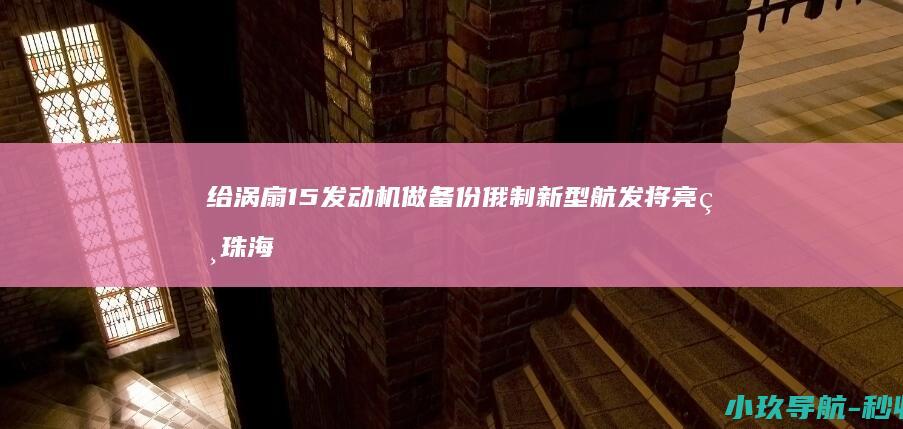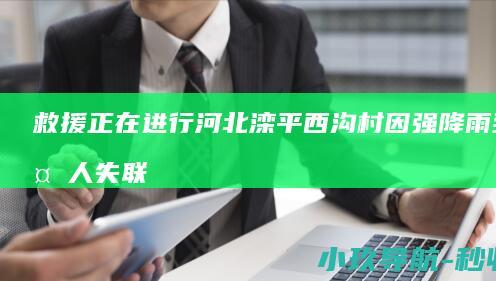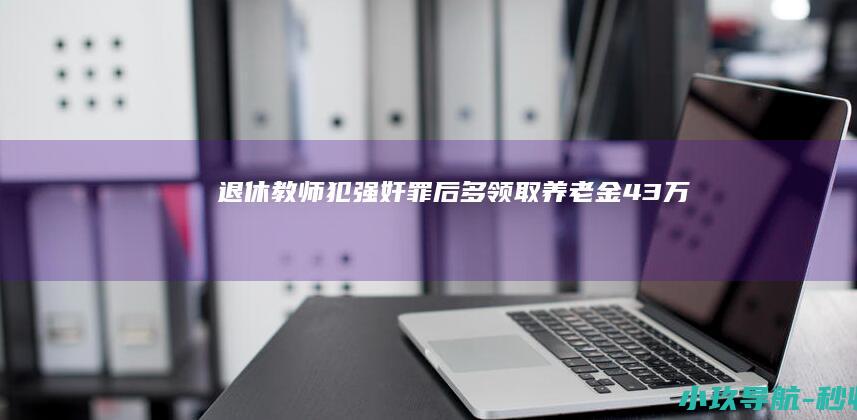流量密码 从鲁迅张爱玲到大湾区文学 许子东解锁现当代文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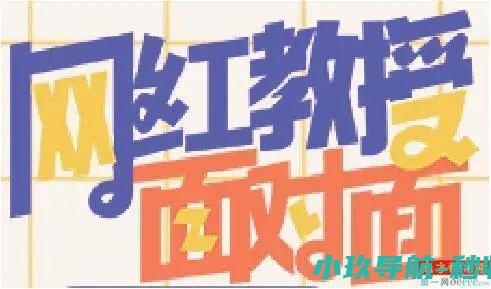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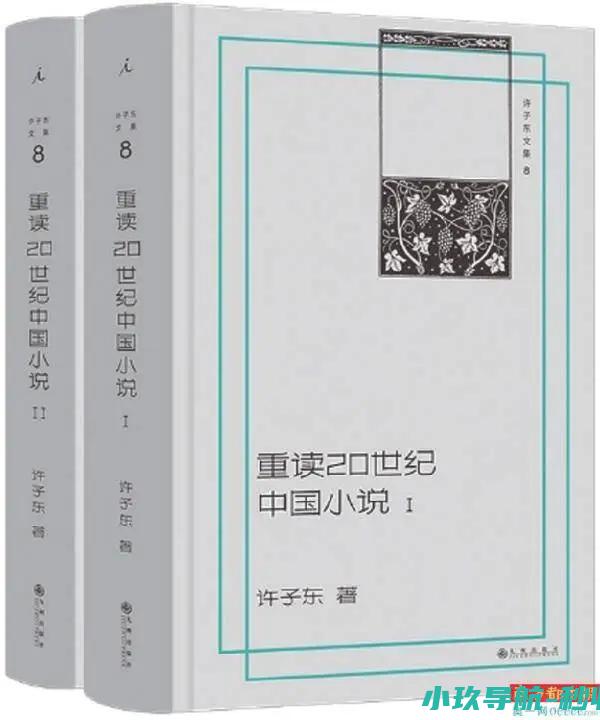
文学教授许子东和他最新个人文集中的《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
7月18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的第35届香港书展上,李欧梵与许子东两位知名学者,展开了一场题为“从鲁迅到张爱玲”的对谈,吸引了众多文学爱好者慕名而来,他们中的很多人是许子东的粉丝。鲁迅和张爱玲如何能够穿越百年时光的长河,在每个历史时期都焕发出超越时代的文学魅力?他们的作品又为何能在不同代际的读者中引发跨时代共鸣?正是这场对谈要探讨的引人深思的命题。
假如鲁迅和张爱玲活在今天?
“他们不仅玩小红书,也许还会直播带货”
讲座伊始,许子东介绍说,如今中国高校中文系的研究题目中,以鲁迅为题的最多,张爱玲位居第二。论及鲁迅精神在当今的影响,“吃瓜群众”便是其体现,“鲁迅早期就刻画过‘围观’的庸众,所以‘吃瓜群众’这四个字的出现,在我看来正是鲁迅精神向年轻人的渗透。”
张爱玲在大众文化中的影响力更是不言而喻。“她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无论好坏都会引发巨大争论,足见其热度经久不衰。年轻人对张爱玲的关注和讨论,也表明当下女性意识的觉醒。”许子东说。
“鲁迅是一座山,张爱玲是一条河”,这是许子东被人反复提起的金句。他回应说,鲁迅背后的那些“山”——茅盾、老舍、沈从文等,都与鲁迅志同道合,他们感时忧国、唤醒民众,“只是鲁迅这座山太高,遮蔽了后面的山,我们很难绕开鲁迅去谈老舍、谈茅盾。”
张爱玲却不同,她另辟蹊径,“她觉得那些宏大问题并非她所关心的,她探讨的是老百姓如何过日子,如同她在《中国的日夜》里所写的买菜途中的市井见闻。”许子东将其概括为:“用日常生活对抗宏大叙事”。这种“山与河”的辩证,不仅是文学史的坐标系,更暗合着当下年轻人“在宏大叙事与个体生存间反复横跳”的精神状态。
AI时代来临,倘若鲁迅和张爱玲活在当下,他们会如何玩转互联网?许子东猜测:“鲁迅肯定会参与其中,不仅会开直播,还会发小红书。”他指出,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有一个重要特点被很多中国读书人传承却未充分意识到,即他既是一流的作家和学者,也是深度介入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批判精神是鲁迅留下的遗产,他曾为当时最流行的报纸《申报》自由谈开设专栏,“放到今天就相当于小红书的热门笔记”。张爱玲肯定也会深度参与互联网,“毕竟她说出名要趁早,说不定还会带货。”
从电视到自媒体时代的许子东:
一个“教书匠”的转型试验
许子东是“1969届初中生”,他的同行里,王安忆、陈思和、陈平原等,都是第一代差不多没怎么读中学的青年人,又是最后一代全体离城下乡的“知青”。他在生产队插秧伤过腰,返城做轧钢工人患了气喘病。曾被公社推荐参加县城高考,填报生物系志愿未果,后被荐入冶金局“大学”,一半精力读电气自动化,一半时间仍在发文学梦,直到失恋,废“铁”从文,“考研”上了华东师大中文系。
他的“张爱玲之缘”,始于新婚之时,当时完全不知情,大学分配的教工房就在1949年张爱玲上海公寓所属的弄堂。后来“洋插队”在洛杉矶,只知神秘的张爱玲隐居于此,但真没想到她最后的住处就在“眼皮底下”,同用一个邮局,同一家复印店,可能还擦肩而过,而他心中正暗暗构思着张爱玲论文。再后来到香港的大学教书,这也是张爱玲生活写作过的城市。偶然,当然都是偶然。
2000年以来,他跨界上了凤凰台《锵锵三人行》,这一上成了“老友记”,反而令几十年教书生涯似乎毫无影响。但他对中国文学一直专注,说到底,“我就是一个教书匠”。从《锵锵三人行》到《圆桌派》,许子东是最早一批进入电视等公共媒体视野的知识分子。流媒体时代来临,许子东又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解读文学经典,在B站、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开设栏目、录制音频节目,既保持了学术探讨的深度,又兼具传播的趣味性,受到年轻群体的热烈追捧,为经典文学的当代传播探索出一条创新之路。正如李欧梵对他的评价:“许子东有一种能力,鲁迅或张爱玲的原话经他讲述,摇身一变,总能产生出奇制胜的效果。”
但许子东对如今“知识分子网红化”也有清醒认知。他看重“身为知识分子承担的社会责任”,这也是鲁迅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遗产。如今的“网红学者”身份也自有其使命,那就是在热搜时代守住思考的底线。
在很多观众的印象中,他是那个“三人行”圆桌上侃侃而谈的“许老师”。“明星嘉宾”的光环,某种程度上遮蔽了他的学术研究成就。随着今年《许子东文集》简体版在内地正式推出,这位在文学研究领域耕耘数十载的学者,再次让大家意识到了他的这一身份。
访谈中,许子东向南都记者透露手头上正在撰写的自传,他将如实书写自己与时代的故事,讲述“废铁是怎样炼成的”。
访 谈
文学既是守望者,也永远需要先锋
南都:今年《许子东文集》简体版在内地正式问世。谈谈这套文集的大致情况?
许子东:理想国愿意出我的文集,是我的光荣。已经出版的有四本,包括《21世纪中国小说选读》《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许子东现代文学课(增订本)》《细读张爱玲(增订本)》。未出版的还有《重读鲁迅》《小说香港》等。有一卷我还没写完,就是我的自传,我要把时代生活的内容再多写一点。
南都:《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是一种新的文学史编写方式,有点另类。你是以独立的作品为坐标。采用这种“以作品为中心”、回归文本本身的细读法有何优势?你怎样去呈现“文学”与“史”的关系?
许子东:往大了说,我认为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对作品的重视不够。你去看现在的文学史,包括教育部指定的文学史教材,大概40%是时代,40%是作家,最后20%是作品,通常大半篇幅都在讲述时代背景、介绍作家生平,比如这位作家一生写了哪20本书。当你想查找具体某部作品的介绍时,即便再重要的作品,在文学史里也只有一段或几句话的描述。这种情况会让学生养成不良的读书习惯,他们可以不读作品,只背诵结论即可。结论的“公式”通常一半以上的作品都能套用。对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子夜》《家》这些最基本的名著,究竟有多少同学能够读完呢?作为一名老师,我深感忧虑。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动机,回到作品本身。这本书里的每篇经典作品是一个点,每个点排列起来,放远了看就是一条线,这条线就是文学史。我也有意地把“作家”放淡一点,“时代”我也不直接讲,讲作品自然会讲到时代。
另外,我是按作品发表时间来排。最后一篇是21世纪初的刘慈欣《三体》,我把它拉上来一点也放进去。很多人说我这是“另类的文学史”。王德威的《中国近三百年文学史》是往外走,他也是另类的文学史。我是不讲作家、不讲历史,直接读作品,也是文学史的另一种路径,因为我这么串起来的文学史,和人家叙述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南都:在《21世纪中国小说选读》中你说“中国当代小说一度是思想解放的先锋,现在是人文传统的守望者。”怎么解读这种小说的社会角色转向?
许子东:这句话讲的是80年代以后的小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等,那时候作家会讨论一些社会上还不大能讨论的问题,比方说恋爱当中的“性”放在什么位置?王安忆、张贤亮他们写,还有很多作品讨论“十年”,或者批评血统论等等,所以我说他们是思想解放的先锋。为什么说他们现在是守望者呢?因为现在在网上最受关注的是两种,一种是流量和八卦,比如某集团原来的老总有几个私生子;另一种是比较极端的声音,在这种时代氛围下,我说当代文学是人文传统的守卫者,是因为他们捍卫了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然后,你想为什么一个人有时候是先锋,有时候是守望者?这就好像一个人站在海滩边上,什么时候他是先锋,什么时候他是守望者,就完全根据潮水的方向而定了。
南都:与此同时,你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年轻一代的小说创作,是否呈现出对故土记忆、传统文化的自觉赓续?
许子东:当然有,这也是必然的。文学有两个基本要点,其一,你必须书写自己所坚信的内容,文学很难投机取巧。倘若有作家来问我:“当下写什么题材能火?”我自然可以告知他,写某类题材必定能火。然而为何无人去写,并非他们不想,关键在于,那是否是你真切的情感?是否源自你真实的生活?
比如回顾“十年文学”,那个时期没有一部作品能够立得住脚,因为那种写作带有明确的目的性。那时可以有小短文、杂文、社论、诗歌,但却没有长篇小说。原因何在?因为作家创作小说,无论你秉持何种思想,归根结底只能写出自己所坚信的、蕴含于灵魂深处的东西。在当今时代,谁不想博取流量呢?但你最多也就制作个短视频,对吧?不可能为了博流量去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正是这个缘故,长篇小说始终坚守着灵魂。
另一方面,写作必定是一种探索。王安忆、莫言这一辈作家仍处于主流地位,而如今的林棹、双雪涛、魏思孝这批作家,他们要写出与前人不同的作品,在写作手法和观念上必须有所突破,得创作出别具一格的内容。所以我说当代作家是人文传统的守望者,这指的是他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至于文学本身,它永远都需要先锋。
从《伤逝》到《倾城之恋》,张爱玲打破五四爱情模式
南都:你说“鲁迅是一座山,张爱玲是一条河”,张爱玲笔下的男女关系颠覆了鲁迅等作家所构建的“启蒙-拯救”爱情故事模式,其对两性关系的祛魅书写引发了跨世纪的共鸣。你认为张爱玲对后来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许子东:这些话是我在上课时跟学生讲的,为了防止学生打瞌睡,我还说巴金是朱古力牛奶,茅盾是卡布奇诺,老舍是红茶,周作人是龙井……结果出版社把我评价鲁迅和张爱玲的这句话摘出来放到了书封上。你也知道,如今大家都热衷于金句,你讲一大串话,别人记不住,就只记住一句金句。
鲁迅是一座山,后来很多作家也如同山一般,都被他的影子所遮蔽,而张爱玲是一条河。现代文学的不少作家,比如老舍、茅盾、沈从文,成就丝毫不逊色于张爱玲。但问题在于,他们对于中国、民众以及自身的看法,都与鲁迅相似,走的都是鲁迅的路子,核心是“感时忧国”,拯救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唤醒民众。所以我说鲁迅这座山太高了,我们无法绕开鲁迅去谈老舍、谈茅盾。但张爱玲不走这条路,她另辟蹊径,难以将她归入哪一类,也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来与她相比较。
举个例子,鲁迅的《伤逝》,男人是读书人,女人负责做饭,能感觉到男人对女人不满,觉得她整天只关注油盐酱醋之类的琐事,似乎读书人就比油盐酱醋要高一等。小说有这样一段,男人说要奋斗、要继续写作,于是推开了桌上的醋罐酱瓶,铺开稿纸。从这个动作可以看出,他要推开“饮食”才能开始写作。这是当时的作家,包括如今很多男性知识分子都有的观念,很多男的文章写不出来,就埋怨老婆把油盐酱醋放在桌上。要是女人跑去问他今晚吃阳春面还是拌面,他会火冒三丈,好像自己很了不起。这样的知识分子我见过不少。
张爱玲采用了怎样的手法呢?在《倾城之恋》里,男人请女人吃了饭、坐了船、开了旅馆,该睡觉了,可男人却把女人带到海边,给她讲诗经。讲完后,那天晚上什么事都没发生。女人回家后有一段独白,我觉得非常经典。她说:原来这个人是要搞精神恋爱,那也好,不搞精神恋爱,多数就是肉体关系,精神恋爱就会结婚,所以精神恋爱也挺好。不过它有个坏处,他说的话我听不懂,听不懂也没关系,以后找佣人、找房子、买家具,不都是女人做主吗?其实她心里在想:你讲的东西我才懒得理呢,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这是女性首次发出如此世俗、如此实际、如此不浪漫的声音。这便是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她打破了“五四”以来基本的爱情模式:男性给女性讲文化、讲知识、讲道理,唤醒女性,而女性纯真善良,被男性的知识风采所感染,陷入爱情;可是,在张爱玲的笔下,女性满脑子想的都是“饭票”,都是极为现实的问题。男性谈爱情、讲《诗经》、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她不太听得懂,觉得只要结婚就好。张爱玲小说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在于她呈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声音。
概括来说就是“用日常生活对抗宏大叙事”。这不仅是两位作家的差异,也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不同。
“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有点成立了
南都:2003年你曾经在一次与黄子平教授的对谈中说,香港作家很少描写社会现实,关注情爱较多;女作家写情,男作家写欲更为大胆露骨。这种情况至今如此吗?
许子东:最近20年我跟进得没那么及时,不敢妄下结论,但大致印象上,我觉得香港文学始终是缺乏一个写实主义的主流,内地是写实主义为主流。香港文学的优点是现代主义试验和通俗文学蓬勃发展。内地虽然也有通俗文学,但是没谁承认,没有哪个作家说我是通俗文学作家,连马伯庸也不承认。其实现在要写香港的现实题材,你可以盯住一个财团写,盯住一个老板写,盯住一家香港企业的深圳分厂写,都有很多故事可挖掘,但是有吗?基本上香港作家觉得自己对社会问题缺乏判断力,所以就避开了。比较能把握的就是我们的楼这么小、我们怎么在电车里拍拖。男的写欲也是之前了,比如昆南、刘以鬯他们这一代,写出来个个男的都是渣男。但现在男作家更少了。所以我在《小说香港》里边的判断基本没有太大变化。
南都:香港文学近20年来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
许子东:我比较注意的现象是,经过大力提倡,所谓“大湾区文学”这个概念有点成立了。现在深圳的高速发展,广州粤语文化的持久存在,使得大湾区文学有很多活动,相关的作品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量,而大湾区文学的核心点是多元,它跟东京、纽约、硅谷湾区的最大不同是,那三个湾区都是单一语言、单一经济、单一货币,而我们粤港澳大湾区语言至少有三种,普通话、粤语、英语,甚至澳门还有葡文,这是很罕见的一个多元文化试验区。
同时,你再看看这几个地方的文学史也很不一样。大湾区的文学史有它自己特点,它跟北京上海都不一样,比较南派一点。像欧阳山的《三家巷》就和“三红一创”不一样,秦牧和刘白羽、杨朔他们也不一样。
南都:除了“大湾区文学”之外,当代小说的地域写作,不仅体现出对本土记忆的深度挖掘,还表现为以地理空间为划分的某些阵营,比如“东北文艺复兴”“新南方写作”等。你如何看待地域书写?
许子东:地域写作也可能有它的局限,比如双雪涛过去的东北写作,如果它主要侧重在20世纪90年代工人下岗的悲剧这一条线,的确可以引起一部分人一段时间的共鸣,但是你得考虑怎么把它放到共和国的历史叙事中。工人不下岗的时候真的就那么幸福吗?你看看上海作家路内写的小说《慈悲》,又不是这么回事了。
我认为地域划分也是一种策略性的探索。批评家如何生存呢?他们要么发掘新作品,要么提出新概念。原本中国的批评家很擅长发明新概念,从1979年到80年代这短短10年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名词更换了七八次,每次都十分热闹。然而9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就减少了。原因何在?因为文学与社会变化的节奏变得较为一致,文学作品不太容易被命名了。无论是“东北文学”还是“新南方写作”,其涵盖的作品都颇为出色,也引发了一定反响,但作为一种文学潮流,这些概念在社会上的反响不够大。我个人觉得,如今社会对文学的关注度已不如往昔,文学领域想要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变得不太容易。
南都:在你看来,近20年来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文学写作现象是什么?
许子东:我在书中也提及了一个概念,名为“细腻写实主义”。我认为,这是近20年来最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长篇小说不再聚焦于情节和人物塑造,而是着重刻画细节、描绘画面。简单来说,就如同《清明上河图》一般。小说里虽有众多人物和故事,却难以找出一条明确的主线。过去的小说像19世纪的欧洲油画,而当下的小说有点像传统中国画,山水多焦点、人物稀疏分散。
“细腻写实主义”的源流可追溯至19世纪末的《海上花列传》,那便是这一潮流的开端。后来的晚清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刻画了众多人物,却没有一个明确的主角。在现代文学里,也不乏这一流派的优秀作品,比如萧红的《生死场》,你很难分辨出谁是主角。然而,这股写作潮流在1949年后又式微了,后来我们倡导的是“典型环境典型人物”。
最近这股创作方向又回归了。实际上,你也可以说它描绘的是典型环境,但它未必着重塑造典型人物, 像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金宇澄的《繁花》、王安忆的《天香》,还有林棹的《潮汐图》、魏思孝最近拿奖的《土广寸木》,都是近年来屈指可数的佳作,它们都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娓娓道来许多小故事。我觉得这已然成为一种潮流,只是鲜有人响应这个概念。
“知识分子必然有专业,同时也有社会责任”
南都:近些年你在不同的互联网平台开设视频、音频节目,收获了很多网友关注。谈谈你对在网络上讲课的看法?入驻B站和小红书的初衷是什么?
许子东:在网络上讲课会稍微通俗一些,但我不会做太多调整。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我的本职是老师,研究的是文学,无论在何处讲学,我都秉持这一身份。当然,我不可能成为所有人的老师,但我可以分享自己的专业见解。
小红书的播客仅有几期,是他们来“哄”我开设的。不过,我还是经常刷小红书的。B站我有一档小说解读的节目。B站的内容丰富,搜索功能强大,但也存在弊端。比如,我们在不同场合说话方式是不同的,像写信、起草报告、接受采访、与朋友聊天等,语境都不一样。如果把不同语境下的话语拼凑在一起在网上呈现,还断章取义,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南都:你是最早一批进入电视等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如今很多大学教授也都有视频账号,在B站、抖音、小红书平台开课。你觉得这是一股风潮,还是真的可能改变学术传播的生态?你如何看待今天学者在公共传播中承担的责任?
许子东:这方面启发我的还是鲁迅。他就有双重身份,一个是作家跟学者,他的小说是一流的,他研究的《中国小说史略》到现在还是一流的学术著作。第二个身份是杂文家,他批评社会、写随想录,按今天的说法等于是开专栏。尤其是后来他花了很多时间去跟人争论、写杂文。他说很多人劝他潜心下来写长篇,他说他也明白别人的好意,但总觉得中国有这么多事情,看到了不写会憋着难受,中国的知识分子钦佩鲁迅也是钦佩他这一点。毛泽东对鲁迅高度评价,说他的骨头是最硬的,是中国新文艺的方向。既是指他的小说,也是指他的社会批判,说他不仅是一个文学家,还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今天中国的读书人、知识分子,主观上也是想走这条路的。你看很多一流的学者,陈平原、赵园、葛兆光,他们除了学术研究以外,也写随笔散文,往往销得比学术文章要好,他们也参与理想国的音频节目,讲的东西跟他们的研究信念、观点和材料还是一样,只是表达方式不一样。
我认为,只要是知识分子,他必然有专业,同时也有社会责任。如果他只有专业,有人说过,那不叫知识分子,那叫专业人士,比方说牙科医生。现在很多人把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活动、表达公共意见看作是一种不务正业、赚钱、贪虚名,其实这些都有,但更重要的是他有他的社会责任,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要是还搞不明白就多看看鲁迅。鲁迅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也是最著名的属于公共社会的知识分子。
南都:今天我们生活在数字生存的时代,面临AI创作、短视频叙事等新技术的冲击,文学或者小说这种载体还能够去有效的表达我们的生存经验吗?
许子东:这个我很难判断。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AI都只是工具,我没有在DeepSeek里查出过任何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东西。但是我看书,不管是看今人的书,还是看古人的书,总有意外的发现,你看庄子、看孔子、看亚里士多德,你都会发现,哇,这么早人家就这么来看问题了。看书永远能看出你不知道的东西。
我觉得AI将来会越来越往几个方向发展。第一,现在很多人AI写作,我相信接下来DeepSeek等应该发明一套工具,来检查这些文章是不是AI写的。这也是帮我们老师做点事情。第二,现在的部分文科如行政管理、文秘等,有很多可以形成规律化的东西,其内容容易总结,就应该多依靠AI,使政府机构有更公开更明智的决策,其实这方面的用处是最大的。
采写:南都记者 朱蓉婷
以"早"为话题的作文,帮我找有哪些题材?
早。 你可以在开头说说早的重要性,然后下一段写写鲁迅先生某天迟到后,在他的书桌上刻了一个早字,便不再迟到。 早起的鸟有虫吃,张爱玲女士也说过出名要趁早,可见早的重要性!事事都早一步于别人,你成功的几率便会大。 虽说枪打出头鸟,但那是不正当的“早”,早也是要分事件的。 不该早的事情不要早,会收益的!最后一段总结一下全文就行了。
爱情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那么多人为它伤心.痛苦呢?
爱情是很复杂的~因为能够有童话般的完美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但是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人们把无数美好的字词附加在她的身上,归结起来对爱情的歌颂与祝愿,无外乎两个字“永恒”。 谁都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份永恒的爱。 年轻的生命总是向往着美丽的爱情。 爱情对于青春是一种心的驿动,是一种难以抑制的青春情怀。 少男少女都爱做梦,做一个童话的梦,做一个爱情的梦。 梦中期盼着童话般美丽纯洁的爱情。 美丽、凄婉的爱情故事《梁祝》,在英台翩然跃入坟中,梁祝化蝶,蹁跹飞舞于人间中实现了其爱的永恒:生不能同衾,死也要同穴!将人们对爱的美好期盼升华到了一个最高境界。 但传说终归是传说,在电影《周渔的火车》里的周渔(巩利饰)有一句对白:“……心里有,才是真的有,心里没有了,才是真的没有了……”你是否知道是什么有或没有呢?最喜欢张爱铃的一句话:为了他的爱嫁给他和为了他的钱嫁给他,本质是一样的,没有谁比谁高尚多少.结婚就是一种改变.而改变首先意味着放弃,一定会为了点什么,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记得谁说过,找个中意的人谈谈恋爱无非是为了让生活增添些乐趣,而找个老公则是为了在生活上获得一个帮手,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单身是一种生活方式,结婚只是另外一种生存方式。 张爱玲在她的《红玫瑰白玫瑰》里说:普通人的人生,再好些也是“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上,就在上面略加点染成为一枝桃花——她的笔原是尖刻凶狠的,想要把人生温暖的面目撕裂开了给人看,但是我依然看到了她理性目光下包涵的是对这个人生最彻底的爱和留恋。 在书中主人公的爱情是无可奈何的残缺和遗憾,选择了红玫瑰就要放弃白玫瑰,反之亦然,人生的无奈,爱情的遗憾写的淋漓尽致.在我们少年时,我们的行囊是空的,因为轻松,所以快乐。 但之后的岁月,我们一路捡拾,行囊渐渐装满了,因为沉重,快乐也就消失了。 我们以为装进去的都是好东西,可正是这些所谓的好东西,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许多烦恼,减少了很多快乐~我们是不是很象爱情和生活的蜗牛?但是我们却没有选择的余地.尽管我明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特别是在这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时代,人生带给你更多的是无奈和辛酸。 为了家你要不惜一切地去奋斗,因为你是爬坡的车轮,没有金钱能活的开心吗?爱情跟金钱到底哪个重要??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尝过才明白!现实的婚姻其实是很无奈的,台湾的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数钱、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去,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 有时候,我们又误以为一种生活的习惯——对一个男人的或女人的,是一种爱情。 最欣赏这句话!!哈哈~~其实这个世界上许多东西正在悄悄地变质。 包括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婚姻。 当人们的心变得躁动不安,当物质生活告别一贫如洗,当金钱以它锐不可挡的气势进入生活,一下子人们的精神世界坍塌了。 我们享受着所有现代化的文明,唯独我们的精神变得无比空虚。 所以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的新名词,离婚外遇一夜情;不管是在现实还是网络,到处充满了暧昧的称呼:知已原来也要分蓝颜和红颜。 曾经恋爱的人都明白,最爱的,总是得不到的。 得与失,得当然喜;得而复失、患得患失、乍得还失,更悲!曾经恋爱过的都明白,童话式的天长地久只属于童话,属于现实,难得可贵。 试问那些或许也想同甘共苦的夫妻又如何躲得过?我情愿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同甘共苦的夫妻,只是那也一定是凤毛麟角,物以稀为贵罢了。 我只想说宽恕、同情、怜悯并且了解和接受人性的弱点吧!面对金钱和爱情难以同时拥有的现实面前,该来的就来,该走的就让它走。 在现实中,面对许多不可能同甘共苦的夫妻,不如只当做了一场朋友,既然缘分散尽,那么就轻松放手,祝愿各自好走!没有人是故意要变心的,他爱你的时候是真的爱你,可是他不爱你的时候也是真的不爱你了,他爱你的时候没有办法假装不爱你;同样的,他不爱你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假装爱你。 当一个人不爱你要离开你,你要问自己还爱不爱他,如果你也不爱他了,千万别为了可怜的自尊而不肯离开;如果你还爱他,你应该会希望他过得幸福快乐,希望他跟真正爱的人在一起,绝不会阻止,你要是阻止他得到真正的幸福,就表示你已经不爱他了,而如果你不爱他,你又有什么资格指责他变心呢?这也许就是爱的悖论。 不管是在虚幻还是在现实,每个人都在寻觅自己所爱,即使已经伤痕累累也无怨无悔.一次次被情所伤,一次次为情所困,所为何来?静下心回忆过往,常常是一声叹息:如果爱痕有迹,迹可寻;如果岁月有音,音可觅;如果憾亦有涯,涯可尽;如果天亦有情,情可续.可是,心如果已在灿烂中死去,爱真的还会在灰烬里重生么?都说是天亦有情天易老,老天尚且如此,何况人乎!你我也许又迷失了,找不到方向.由于人世间有一情字,就注定了有很多人会为情所伤。 因为童话般的爱情注定是一个美丽的童话,而且感情这东西的确是很伤人的,因为它的敏感与细致,爱到极致,就是毫无保留,即使是对自身的防御.有人说,感情向来都是一个双面的刃,即可伤害别人也可以伤害自己,它可以有光华耀眼的美丽,也会有让人锥心刺骨的痛楚.其实,每个人都知道,一个值得爱的人并不是很容易找到的,有时候即使是花一辈子.寻找这个人是很辛苦的,会有烦恼,会有忧愁,会有彷徨,会有失落,但千万不要让自己和对方受伤。 其实我可以举的例子真是太多,但我现在却一个也不想再说了。 在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中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最幸福;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所有的美梦是好的,只要没有破灭~~否则,钱是要紧的!”他老人家一生其实也是在无可奈何之中度过的,所以他老人家好现实哦!
什么叫做经典?
什么是经典?(1)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后人尊敬它称之为经典。 (2)经典是指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 (3)经典就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书”。 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那些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就是经典。 尤其是那些重大原创性、奠基性的著作,更被单称为“经”,如老子、论语、圣经、金刚经。 有些甚至被称为经中之经,位居群经之首,比如中国的《易经》,佛家的《心经》等,就有此殊荣。 由此而论,,,,鲁迅的作品是中国的经典.《荷马史诗》,《悲惨世界》,《和平与战争》巴尔扎克的作品,马克。 吐温的作品是外国的经典。 作品成为“经典”是有“永恒性”的。 作品只有在历史的考验中,被广大求知者认可从而成为“经典”。 至于金庸和张爱玲,他们的作品正在接受历史和人民的考验,但还没有成为“永恒”。 所以有人加了一个定语,称“百年经典”,也是“偷换概念” 而已。
本文地址: http://www.xiaojiuz.com/zuixinwz/8082e2a6f4933441c4f0.html